26日,由中国林学会、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主办,武汉市公园协会承办的“首届中国自然教育大家谈圆桌会议”,在武汉市解放公园美好生活共享空间举行。来自国内科学领域的10余位知名专家学者,围绕“大城市自然教育的可持续发展”主题,从科学、文化、自然、教育等方面,对中国当代自然教育的发展方向展开讨论,并对多次被点赞的自然教育“武汉样本”进行了剖析。
这些科学领域的“大咖”包括:中国科协首席科学传播专家、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主任陈进,清华大学科学史系主任吴国盛教授,清华大学刘兵教授、吴彤教授,北京大学刘华杰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刘孝廷教授,北京林业大学张志翔教授,中国科技出版社副总编辑杨虚杰,华中科技大学向德平教授。他们对自然教育的思辩、追问和探讨,屡屡碰撞出耀眼的思想火花。

市园林和林业局公园管理处处长唐闻,以“相信种子的力量”为主题,讲述了武汉自然教育从起步到发展、壮大的过程。她坦言,武汉的自然教育探索,就是从一粒朴素的“种子”开始,然后 “发芽”“开花”, 逐步系统化的一个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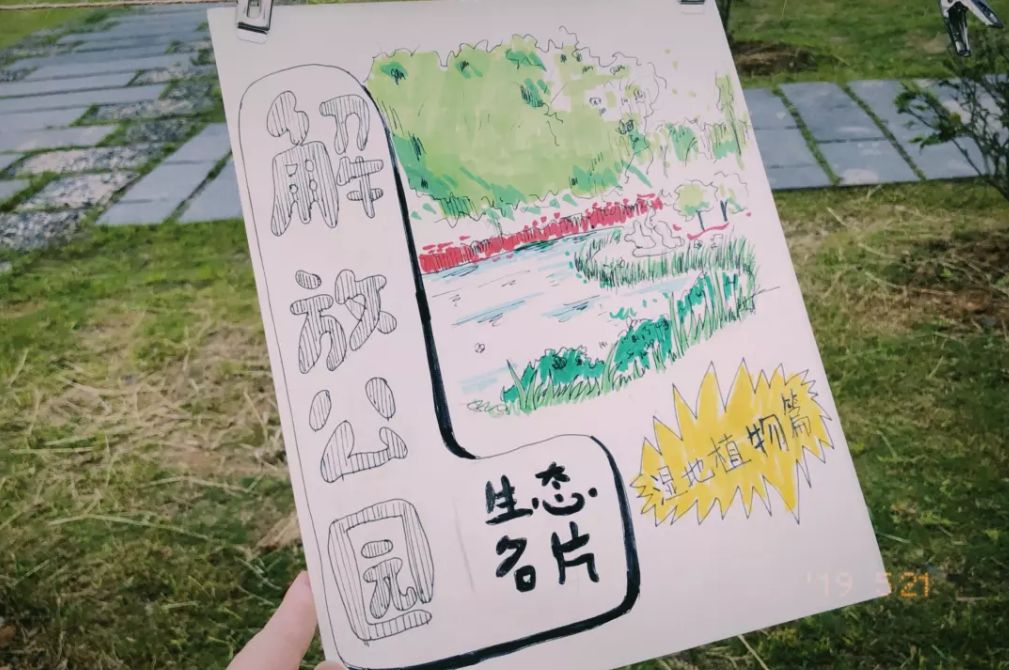
这粒“种子”就是一个有趣的故事。2016年初,三个女人坐在一间小小的办公室里,谈论自然、童年和成长。越聊认识越趋同:“没有自然的童年,不值得称赞。你不了解的故乡,就是他乡。”“把城市的孩子还给大自然,找回大人与小孩、童年与自然、城市与生活本应有的连接。”

当年1月17日,由市园林和林业局、长江日报联合出品的“公园大课堂”推出第一课。截至目前,公园大课堂累计开讲1500余场,1.7万家庭参与其中。并衍生出“植物导师课”等自然教育品牌,催生出沙湖公园“梦想花园”“儿童梦想农场”等实体项目,出版了《一本会发芽的书》《一本会开花的书》等自然教育读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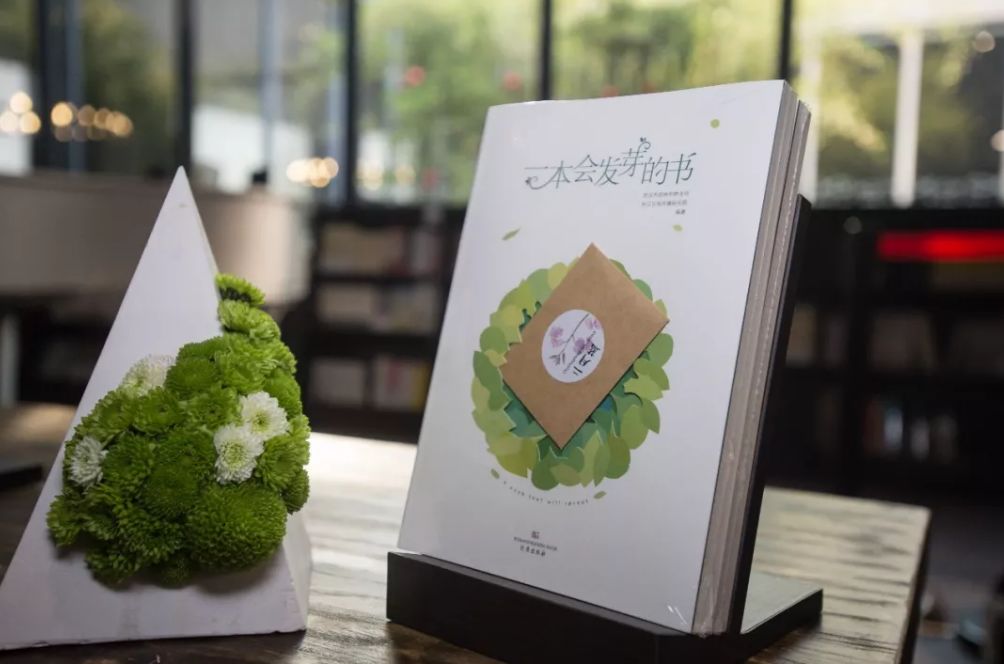
2018年初,随着武汉市教育局和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的加入,武汉自然教育突破公园大课堂周末“兴趣班”的性质和服务规模,形成了真正的“自然+教育”模式,确立了武汉自然教育的第二个主打品牌——中小学生绿色生态研学。150所试点学校30万学生和32个城市公园结对,使公园真正成为孩子们接受自然教育的第一站。

此后,武汉“自然教育”不断“开疆辟土”,向社区“绿色驿站”、自然保护地、产业营地拓展,并由中小学生覆盖到全年龄段人群。全市可供开展自然教育活动的阵地达500多个,组织开展较为集中的自然教育活动1万余场次,接受教育和参与活动人员累计达400万人次。从而形成了一个“政府支持、机构参与、普惠公众”,可复制推广的“自然教育城市模式”。
会上,专家学者们就中国自然教育的发展现状,未来应走的道路,畅所欲言,妙语频出。并且建议,起草《自然教育武汉宣言》。
市园林和林业局局长周耕认为,自然教育具有自然性、科学性、人文性、公益性、社会性等特征。就自然性而言,自然教育首先是在自然中受到教育,然后是受到自然的教育,再就是自然而然的教育。他希望武汉能形成一套科学的自然教育教材体系,有一个机构能统筹各方资源形成合力,进一步推进自然教育的发展。
专家观点

中国林学会副会长马广仁:
武汉是自然教育优秀范例
自然教育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工程,是建设美丽中国的迫切要求,对全世界形成敬畏自然、顺应自然、尊敬自然、保护自然的良好风尚,具有基础性战略性质。
今年4月11日,中国林学会自然教育工作会议上,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发布《关于充分发挥各类自然保护地社会功能大力开展自然教育工作的通知》,中国的自然教育正以星星之火成燎原之势,在全国各地迅速展开。
其中武汉是一个优秀范例,武汉市园林和林业局勇于担当,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鼎力支持,加上全市公园、学校和专业自然教育机构的积极参与与实践,主流媒体大力宣传倡导,初步构成了一个具有张力和成效的自然教育事业共同体,其经验值得总结和大力推广。

中国科协首席科学传播专家、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主任陈进:
科学教育目标,很多可以通过自然教育实现
狭义的自然教育与西方的户外教育相似,希望通过加深孩子与大自然之间的联系,解决他们在成长当中的体能、发展上的诉求,加深他们对自然的了解,培养亲近自然的习惯。
自然教育与科学教育有重合的地方。科学教育主要有三大目标:一是学习科学知识,培养科学精神;二是学习科学方法,形成求真、批判的思维方式;三是培养科学家,甄选优秀人才。这些科学教育的目标,很多也可以通过自然教育来实现。
自然教育的职责,首当其冲应由教育部门承担。但也需要教育体系外和体系内相互配合,互相支持,全社会共同推进。

科学史家、清华大学科学史系主任吴国盛:
自然教育应与四种教育结合
一是与正规教育结合。自然教育只有得到教育局的支持,有具体政策支持,比如将其纳入学分或必修课,才能避免边缘化。
二是与科学教育结合。广义的科学教育其实包含自然教育,但现在科学教育慢慢偏向数理化实验科学。博物学的复兴可以让科学教育回归平衡。
三是与公民教育结合。现代文明的特点之一就是公民教育,中国文化要转型成为现代国家,公民教育是非常重要的。自然教育是要达成人与自然和解、现在的人与未来的人和解,这里的平等思想,恰恰是公民思想的根源。
四是与人文教育结合。自然和人文本就是密不可分的,大自然因为美,才能引起人类的注意。园林本身也蕴含着很多人文因素。

博物学家、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刘华杰:
每个城市应探索最合适的自然教育模式
自然教育的推广应该注重三个方面:
一是因地制宜。“武汉模式”虽已较成熟,但不能全国按照一个模式推广。每个城市都有自身天然的优势,我们只需传达核心的理念,大家自己探索最适合自己的模式。
二是引导公众自我教育。自然教育现存的问题是动力不强,现代人时间少,只有自己喜欢的东西才会主动去学。老师不可能去教所有的知识,最理想的状态应该是引导公众喜欢大自然,从而让大家进行主动学习、自我教育。
三是NGO组织参与。教育部门推动自然教育会面临师资短缺问题,所以一定要和社会组织合作,可以采取国家购买、NGO组织运营的方式。

科学哲学家,清华大学科学史系教授吴彤:
与环境保持亲密关系,物理空间变得有意义
在现代科学里,我们将生活的空间看成是均衡的、整齐划一的物理空间,但实际上空间不仅是一种物理空间,更是文化空间。
人类实际上都是有着地方性的地方人。一个人离开很久,但仍然对家乡有一种亲近感,这是因为他了解家乡的植物、鸟类……通过与周遭环境保持亲密的关系,从而了解一个地方的文化特征和生存的意义,物理空间也由此变得有意义。
科学教育将人培养成整齐划一的人,而地方性知识研究是根植在大地之上的情感认知方式,这种认知方式不一定比科学的理性认知方式差,这样培养出来的人是有个性、有温度和情怀的。

科学史理论家、清华大学科学史系教授刘兵:
真正的改变需要思维的根本转变
近些年,社会责任和环境教育已经列入到正规教育里面,总的来说是教育的一个很大的进步。但目前阶段,自然教育中,非正规教育还是占据了主流。自然教育究竟能够推进到什么程度,正规教育还是起着决定性作用。
社会公益基金会、园林局做好自然教育也是义不容辞,但如果教育部门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那就更好了。而真正的改变需要思维的根本转变,这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任重而道远。
除此之外,自然教育应该面向普通人。对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言,公民保护自然、保护环境意识的提高,比再高的科学技术都有用。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刘孝廷:
自然教育的时机,应该从儿童开始
不同年龄段对世界的感知方式不一样,人的很多情感和感知世界的方式都是在儿童时期形成的,因此自然教育需要讲究时机,应该从儿童时期就开始。
儿童时期的自然教育和科普教育并不矛盾,最重要的是要按照孩子的天性去教育。在这个时期能背几首诗并不重要,培养孩子热爱家乡、热爱花草、热爱大自然才更重要,到了一定年龄再去培养他的社会伦理、科学伦理。将最基本的东西保存住,这样的孩子才是完整的。
地球是我们的家园,但很少有人会像爱家一样去爱它。如果从小就让孩子们亲近自然,那么他们自然会感觉到他和自然界是一体的。

北京林业大学自然保护区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志翔:
认为杨树飞絮扰民是对杨树的误解
最近,杨树飞絮这一最自然的现象,却引发了全社会的讨论,还有很多市民进行投诉。其实杨絮不会引起任何过敏,这是医学界有证据的。正是因为大家缺乏自然教育,对自然事物不理解,对杨树不理解,所以觉得它扰民了,这是对杨树真正的误解。自然教育能够帮助人们化解担忧,正确认识周边的事物。
正规教育体系里的文理分科,让很多学生偏科严重,基本的地理、生物知识都不懂。不应该将自然教育有意割裂,自然教育对人的世界观的形成,对增强人对自然的感知、综合理解等方面,都有着重要的作用。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副总编辑杨虚杰:
武汉作家可写写武汉的乡土植物
目前,自然教育类的图书比较缺失。中国科技出版社最近想引进《解说我们的遗产》一书。内地现在还没有这本书,在台湾可以找到,可以发现这本书的译者,都是学习环境教育或环境解说的专业。由此可见,自然教育是一门学问,而且门槛较高。在未来我们应该考虑让其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要有长远培养人才的打算。
我这里有一本《怎样识别植物》,1977年出第一版,第一次印刷就达到了58000册,这说明公众对于植物、自然天生是有好奇心的,随着近年来自然教育的重要性慢慢凸显,亟需更多高质量的出版物来唤醒公众的兴趣。其实,我们有很多资源可以转化为自然教育的资源,比如《红楼梦》中的植物和金陵十二钗命运之间的关联,就很有意思。武汉有许多本土作家,他们也可以来写一写武汉的乡土植物。

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向德平:
自然教育是和自然的一次协调
我是做社会学和哲学的,在城市社会学里,很重要的一点是城市的生态。现在的城市是一个完全人工化的环境,自然、水、空气……几乎所有的自然因素都被人为的建筑、设计、规划改变了。自然教育就是在人工环境里和自然的一次协调。
不仅我自己,我相信整个社会都希望城市更加包容,让各种各样的自然因素能够与人类和平共处;我们还希望这个城市有温度,有灵魂,不是物质和财富的堆砌物,还能满足人们的真正的需求。
(编辑:张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