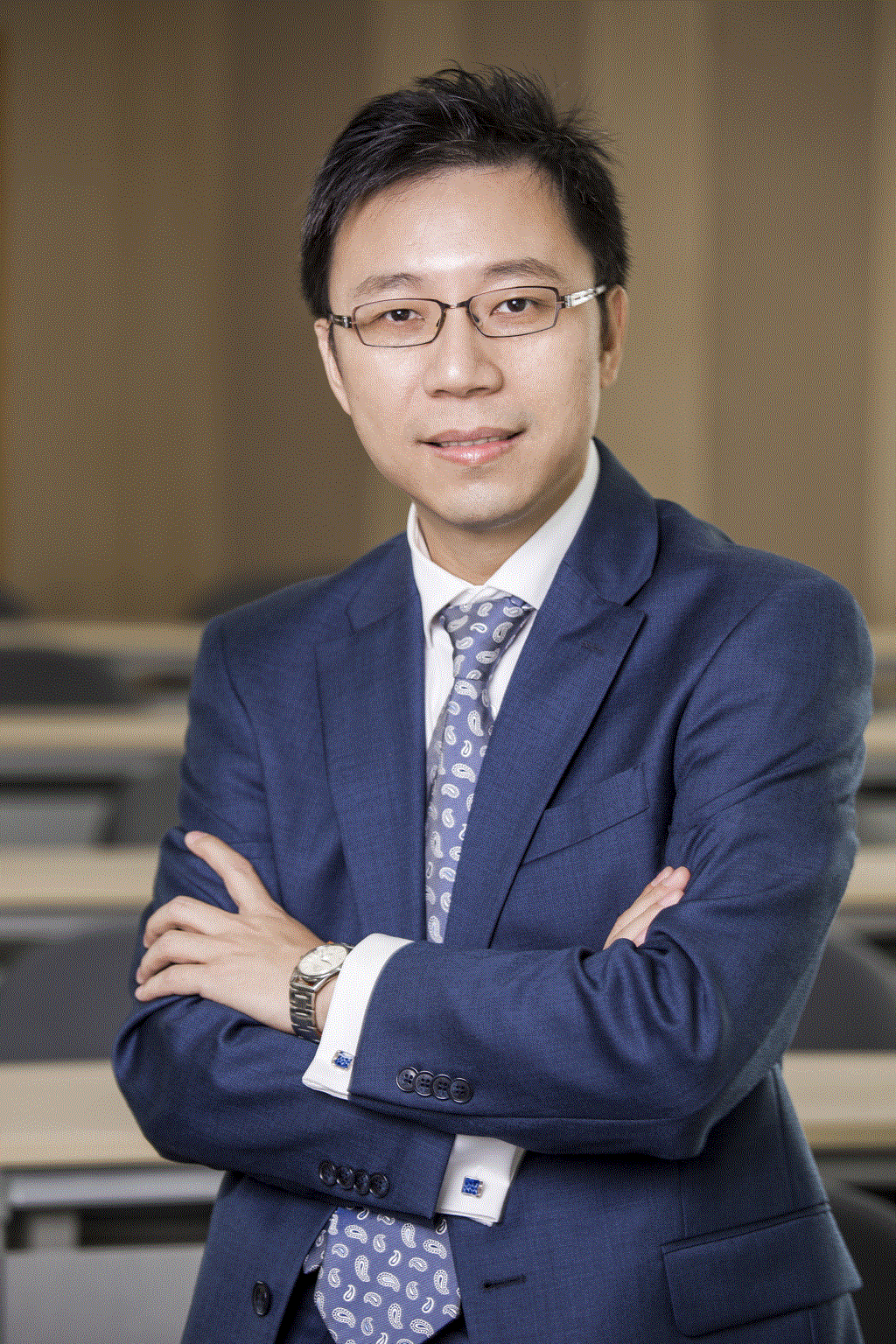
陆铭
长江日报融媒体12月4日讯(记者欧阳春艳)中国城市化进程刚刚过半,“城市病”已经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尤其是北上广深等城市,人口大量涌入,雾霾、拥堵等环境和交通问题越来越严重。在世纪文景出版的新书《大国大城》中,上海交通大学经济学教授陆铭尝试给出自己的解决之道。2日,长江日报记者专访了陆铭。
小故事中孕育着解决大国发展难题的答案
看过《大国大城》后,经济学家汪丁丁这样评价:“这里的经济学叙事,充分超越了教义主义的经济学。中国经验,在陆铭的叙述里,不再是经济学教义的中国脚注,也不再是经济学家读不懂的中国传说。”
作为经济学家,国内外经济学组织中活跃着陆铭的身影,他现在执教于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同时受聘于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和日本一桥大学等多所高校,担任客座教授,并曾担任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咨询专家,参与国际合作研究课题,他还是知名经济学刊物《经济学(辑刊)》的副主编。
作为注重实证、关注公益的知识分子,陆铭游走在中国中西部的广大地区,与当地干部群众交谈,掌握中国经济发展中最鲜活的第一手资料;他用画笔、相机记录下当代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故事,并乐于将这些故事分享给那些渴望了解它们的人。
在陆铭看来,这本《大国大城》正是他多年心血的结晶,是一本写给普通人的经济学著作,这里不仅论述了他对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多年思考,也记载着发生在他身边的故事,“80后”朋友的就业选择、出租车司机的疑惑……正是在这些故事中,孕育着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以及解决大国发展难题的答案。
大城市对年轻人依然充满吸引力
在一场学术讲座中,一位听众站起来问陆铭:我可能要离开上海了,但我还是想知道,居住成本为什么成了现在这个样子?这个状况对中国、对上海的未来,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陆铭的答案是:“上海太小了。”他说,中国的问题不是经济太集聚了,而是长期以来,人口的集聚未能与经济集聚同步。除了出示发达国家高塔一样的经济积聚程度示意图,他还给出了逻辑清晰的解释——不同地区的区域位置决定了各地有不同的比较优势,适合发展不同的产业。某些产业,譬如制造业、服务业,有规模经济效应,人口集聚会伴随着更高的人均GDP;而对另一些产业,譬如农业、旅游业、各种资源型产业,受到自然资源的制约,如果要提高人均产出,必须减少人口。
前几年,迫于大城市的生活压力,一些年轻人“逃离北上广”,但是最近两年,“返回北上广”又受到热议。大城市对于个人发展的积极作用,再次引起了人们尤其是年轻人的关注。
“逃离北上广”之后,人们发现,生活并未变得容易和舒适。而在大城市,虽然要面临种种压力,但是相对公平的竞争环境、有序的公共服务、丰富多彩的城市生活、国际化的视野和机遇,对年轻人仍然充满了吸引力。
在集聚中走向平衡
在《大国大城》中,陆铭对大城市的发展机遇进行了理性总结,他认为,来到大城市中发展,发展大城市,不仅对于个人来说是有益的,而且对于整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经济结构的转型,都是必然选择。
陆铭以三个关键词总结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核心秘密。这三个关键词分别是密度、距离和分割。
大城市更大的人口密度,彰显了规模经济的优势,比如分享固定投入、更好的劳动力市场匹配、获取人力资本外部性等;而基础设施的建设、互联互通水平的提高,经济和时间距离的缩小会导致生产要素向大城市的集中;而取消经济发展的区域分割,促进土地、劳动力、资本三大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使其向经济效率更高的地方转移,是提升整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核心所在。
同时,经济的集聚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可以实现在地区和城乡之间“人均GDP”意义上的平衡发展,从而迈上一条在集聚中走向平衡的道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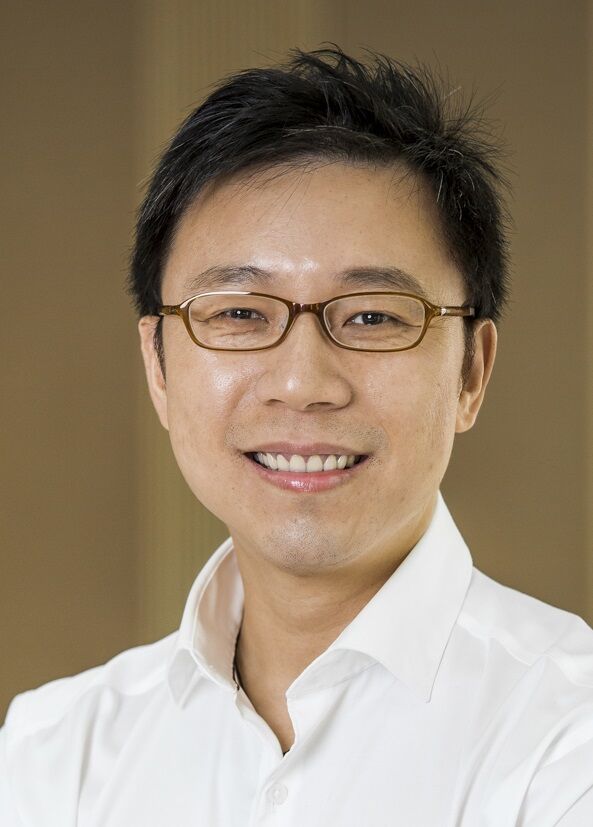
访谈:宜居大城:活力、便捷和环保
城市规模与人口流动
读+:为什么人会源源不断地进入到大城市呢?
陆铭:从全世界的发展趋势角度来讲,人源源不断地向大城市集中,主要还是因为现代经济发展有规模经济,规模经济既会带来大城市更好的就业机会、更高的收入,也会带来大城市更好的服务质量。而且大城市由于规模经济也会产生更多的服务多样性,它对于生活质量的提升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品质。
再具体到各种各样的人。一方面大城市能够为大学生等高技能劳动者提供学习机会,包括跟别人交换信息和知识,产生创新等。同时大学生向大城市的集中,又带来大量的对低技能劳动者的需求,因为他们需要在工作里进行配合,需要低技能劳动者做些辅助岗位的工作。如此一来,大城市对高技能劳动者有需求,同时也对低技能劳动者产生大量需求。
读+:你怎么看北上广等特大城市或超大城市的人口规模问题?
陆铭:我讲过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全世界是有一个经验型的定律,就是越大的国家,大城市的人口是越多的。在一个市场经济国家,一个大城市的人口有多少是由这个城市的产业结构所决定的,如果一个城市的产业需要有大量人到这来就业,那么就会带来人口的流入。
但是在人口流入同时,通勤时间在大城市会长一点。那么当大城市生活和工作的成本,比不上在大城市进行工作换来的收益时,人就会停止向大城市流动,这时候大城市人口规模就定下来了。
读+:在中国,人口不断向大城市聚集的现象什么时候可能停止?
陆铭:全世界不要说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在向大城市集中,就算发达国家已经完成了城市化进程,现在在东京、纽约、伦敦,人口向这些地方集中的过程都还没有停止。以东京为例,东京在经济高速增长,城市化率不断提高的那段历史时期,人口有过一个非常快速的增长时期。但是进入到1980年代,它的城市化进程开始放缓了以后,人口增长是慢下来了。但是哪怕到今天整个日本的人口已经负增长了,东京都市圈人口已经超过3700万,东京人口还在进一步的往上增长。
中国现在首先是个发展中国家,城市化进程还在推进,人口的增长怎么可能停下来?等到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完成,比如到2040年左右,那么可能一些大城市人口增长会慢下来,但并不意味着人口就会停止增长。
小城市也有小城市的问题
读+.什么才是真正宜居的大城市呢?
陆铭:大城市的宜居,就是要兼顾活力、便捷和环保三个目标。所谓活力,是大城市最重要的宜居,就是它有强大的创造就业和收入的能力,同时它有强大的提供服务的能力,创新能力,能够满足人的消费服务多样性的人性基本追求。
大城市宜居的第二条是便捷性,公共服务比较好,医疗教育资源比较好,通过基础设施的建设来让便捷性提高。
第三个就是环保,大城市的环保不是建大型绿地的概念,而应该是立体式绿化、屋顶绿化、建筑外墙绿化,还有就是在生活中要更多地强调低碳出行。
读+:为什么前一段大家在提“逃离北上广”,现在又有“返回北上广”之说?
陆铭:这还是因为很多事情大家没有看明白,大城市一定是好和不好并存的。很多人看到大城市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房价高啊,比如交通拥堵。因为这些问题离开大城市到了小城市,但是就业机会怎样?收入怎么样?房子便宜一点,但是消费服务业怎么样?小城市人情关系特别重要,能适应得了吗?小城市也有小城市的问题,所以才会导致又“逃回北上广”。
读+:为什么最近全国各大城市的落户政策都在争相向教育水平高的人倾斜?
陆铭:这件事情要分两面看。好的一面,这说明各个城市都是非常重视人才了。事情的另一面也需要注意:每个城市有各自的比较优势,有的城市具有发展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的机会和条件,那么它发展的时候就需要有更多大学生;但有的城市比较有优势的是一般性的制造业或者是旅游农业,它对大学生的需求和创造就业岗位的能力就不够。那么一个城市到底应该是由产业来决定人才的需求总量和结构,还是应该先把人招过来,最后有可能是没有相应的产业给他提供这个机会,我想这个答案应该是非常清楚的。
“城市病”主要不是由人造成
读+:“城市病”是不是因为人多造成的?
陆铭:“城市病”主要不是由人造成的,但我不能说成是并不是人多造成的。这要具体分析是什么样的“城市病”,以及产生“城市病”的原因。比如说一个城市的房价高,是因为有人口流入,还有就是一个城市的通勤距离长,那么跟人多也有关系。
但是,我们一直在忽略供给方的原因,比如说人口带来的住房需求,如果你增加住房供给,是不是房子就可以不要那么贵;大城市通勤时间是会更加长一点,但是这也跟我们的基础设施没跟上有关,比如说地铁的建设速度偏慢。
再比如城市规划里出现的问题,我们一直在讲城市人口疏散。根据我的研究,大城市大量的就业岗位是集中在市中心,优质的中小学教育资源也集中在市中心。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做人口疏散,让人住得离市中心更加远,就会导致人的上班通勤距离是更长了。
我们再来看西方发达国家,伦敦、东京、洛杉矶等,这半个世纪以来城市人口都是剧烈增长的。但这些地方现在变得又干净,通勤也不拥堵,因为他们现在地铁出行是主要方式。所以你怎么能说这个“城市病”仅仅是人口增长的问题呢?
读+:公共服务与城市化之间存在着一种怎样的关系?
陆铭:这要看是什么样的城市。有些城市因为有发展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机会,它的人口是流入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公共服务的资源增加,那么政府可以在发展的过程当中,为人口提供更多的服务。同时在人口流入地,外来人口也为这个城市做贡献了,所以公共服务要强调公平性,要覆盖到常住人口,这也是符合我们国家最近在提的,农民工市民化这样一个发展方向。
但是在人口流出地,因为人口相对减少,它会带来公共服务提供的财力不足的问题,因为毕竟公共服务的提供包括教育医疗等都是有规模经济效应的。这时候从国家的财政转移支付角度来讲,就要更多帮助欠发达的人口流出地去提供教育医疗、卫生这样的公共服务。
以上道理其实也适合于分析大城市与小城市之间,农村和城市之间。
读+:解决“城市病”的出路在何方?
陆铭:解决“城市病”要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不是去控制需求,这也是世界上的普遍经验。“城市病”无非就是交通拥堵,环境污染,房价高涨等问题。交通拥堵,主要要靠地铁建设,用高密度的轨道交通来解决,提高轨道交通占比。同时就是宽马路的模式要改变,要提高小马路的比重来进行分流。发展小马路的街边店,会缩小大家的通勤半径,也可以让交通拥堵得到缓解的。
环境污染靠产业结构调整。如果一个城市,特别是超大城市制造业的比重逐渐下调,服务业比重逐渐上升了,环境污染就得到解决,同时当轨道交通占比提高的话,尾气排放减少也可以带来环境改善。
房价,主要得靠供给方的改革,比如说增加土地供应。在有条件放松容积率的地方,可以适当的放松容积率的管制来增加住房供应;目前已经破题的增加租赁房,也是解决房价问题的一种办法。
【编辑:陈智】






 关注
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