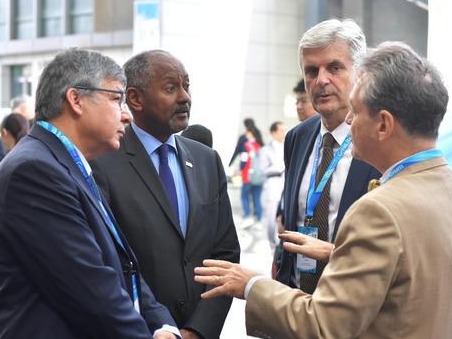阅尽沧桑的布罗代尔对台下一帮听课的年轻史学家们,不无狡黠又不无感伤地说,小子们,我看到太多的变化,可最终觉得什么都没变。意志坚定的改革也罢,摧枯拉朽的革命也罢,只如漂在河上的木筏,看得见上下沉浮,却看不见前行后退。深层历史就像载舟的河水,流速几乎察觉不到。这是历史学家最大的悲哀,历史总给他以前行的错觉。
布罗代尔研究的是长时间段里的历史变化,说是变化,更多的其实是亘古不变,他称为深层历史。对深层历史而言,十年百年的跌宕起伏,都只是溪水过山时的喧嚣,平复之后,依然故我。“遥远的过去和当今之间,决不会有完全的断裂、绝对的跃变。往昔的所为不断延伸到现时生活中来,也不断扩充它。”总之,过去活在当下,当下也活在过去。
深层历史,徐勇称为底色,他说底色决定特色,就像是说过去决定现在,传统社会决定现代化。
想想这话,有了一丝布罗代尔式的悲哀;也有了另一丝的平和。既然无旧邦不新命,无底色非特色,在没有深刻理解阐释旧邦之前,不轻易简单论断新命;在没有彻底搞清楚底色之前,不盲目追求特色,那么就少了颟顸粗暴,多了不着急从容不迫。急,是历史的大忌。调查不深,认识不足,理解不透,就仓促上马,照搬理论,自然受阻受挫受害。这一点,中国农民感触最深。
俗话说,消停作好事;又说,事缓则圆。清代的申涵光在《荆园小语》里解释说:“若急遽苟且,但求早毕,以致物或不坚,事或不妥,从新再作,用力必多。是求省反费,求急反迟矣。”每一次的变革对于深层历史而言,只如秋水入海,望洋兴叹。在它面前,瞎胡闹不得,瞎折腾不得,瞎指挥不得,一句话,急不得。
冯友兰说,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翻译成大白话就是,不着急,听听传统怎么说。文/周劼






 关注
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