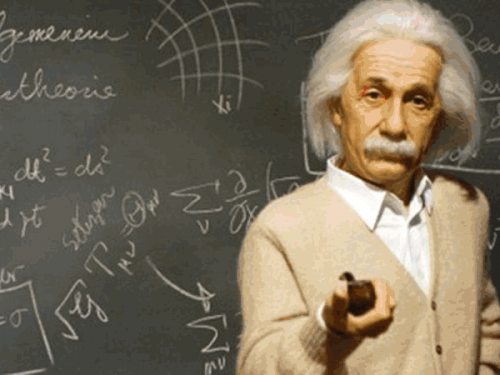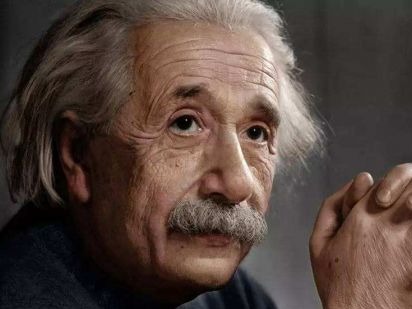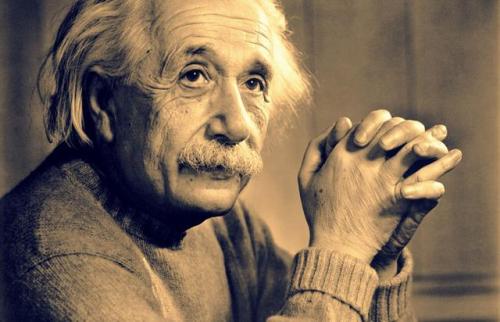周劼 资深媒体人,业余从事文史、艺术研究。
长江日报-长江网讯 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所预言的光线偏折被日食观测证实,一时报纸大肆宣传,洛阳纸贵,据说英国塞尔福里奇百货公司将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论文一页一页贴在橱窗上供路人观赏。
消息传到数学圣地哥廷根大学的数学“教宗”希尔伯特耳中,希尔伯特研究过广义相对论,不禁赞叹道:哥廷根大街上每一个中学生对四维几何的理解都比爱因斯坦强。然而是爱因斯坦,而不是数学家,做出了他的工作。
等等,这话是赞叹吗?怎么听着像讽刺啊。不错,在数学大师的言语里,讽刺说明还入法眼,揶揄便等同赞美了。
这话要分两截子看。一截是爱因斯坦相对论中的数学水平。另一截是哥廷根的数学水平。
爱因斯坦从学生时代,数学就没学好,他的狭义相对论用了极简单的数学,这点简单的数学成为他的大学数学老师闵可夫斯基在课堂上经常拿来的自嘲话柄,老闵对学生说:爱因斯坦如此深刻的物理理论的数学表达式又如此粗糙,我要检讨,那是我教的。
老闵后来用张量数学将狭义相对论方程规范化,成为狭义相对论的标准形式。对于闵老师所使用的数学方法,爱因斯坦刚开始并不接受,认为把相对论转成张量形式,完全是知识多余的卖弄。但数年后,爱因斯坦才明白张量方法的优越,他自己也开始采用张量方法。再数年,他真心感谢闵老师为狭义相对论向广义相对论的过渡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就此说了句有名的隽语:数学家用那么复杂的语言来描述相对论,物理学家简直弄不懂了。
而另一截,从高斯、黎曼、狄利克雷和雅可比,到希尔伯特和克莱因,哥廷根大学数百年一直是数学领域的最高殿堂,一般学子心目中,到哥廷根不是去学习的,是去朝圣的。
至于哥廷根中学生的数学水平,有一则流传很广的轶事可见一斑:一个哥廷根学生,边走路边沉思,突然绊了一下,跌倒在地。旁人跑上去想扶他站起来。他却仍躺在地上,很生气地推开伸过来的手,说:“别来打扰我,我正忙着呢,我刚刚想通一个出色的答案。”
轶事未必真,但这则轶事可信度很高。这样学术氛围里的学生,连“中学生对四维几何的理解都比爱因斯坦强”,并不夸张。
以最高的数学碰上最高的物理学,决战紫禁城之巅,胜负不用想。如果有科学鄙视链的话,第一环一定是数学家瞧不起理论物理学家,就像谚语说的,物理学家听数学家的,数学家听上帝的。反之,对理论物理学家最高的赞美一定来自数学家。
注意,此处的赞美得打引号,数学家的赞美怎么会同于世俗的说好听的话,批评、质疑、鄙视、怒怼,对科学而言才是最需要的,一切的赞美应该让被赞美者认清自身的现实、自我的局限。就希尔伯特而言,他注重数学的公式化和推导严密性,拿数学的精致看物理学的粗糙,简直是“天然色,天然态,花样娇,柳样柔”的美女和“青处青,紫处紫,白处白,黑处黑,恰便似成精的五色花花鬼”的丑女一起上街购物,残酷地陪衬加对比。
但希尔伯特对爱因斯坦物理学思想之深度和广度也是叹为观止的,希尔伯特另一次还讲过:“你们知道为什么爱因斯坦能够提出关于空间和时间最富原创性和最深刻的思想吗?因为他没有学过任何关于空间和时间的哲学和数学。”紧跟直觉,原创的想象力,不羁思考,希尔伯特在爱因斯坦身上看到了“不受教”的野性。
如另一位哥廷根数学家外尔所老实评价的,“物理学家身处由杂乱无章的实验事实建构的迷宫之中,而这些实验事实,变化多端,稍纵即逝,面貌也日新月异,轻重缓急转换频繁,迷宫之出歧路纷纭,迷宫之行道路多艰,因此……爱因斯坦和玻尔之类物理学家,在黑暗中摸索前进,建立起广义相对论和原子结构的观念,他们所运用的经验和想象力与数学家们截然不同。”
两厢结合,来回拉扯,赞美也像讽刺,讽刺也成赞美,就变成了希尔伯特对爱因斯坦亦赞亦刺,亦庄亦谐的评价。
爱因斯坦的待遇还算好的。另一则轶事,希尔伯特听完应用数学家、控制论创始人维纳的学术演讲,说:“我想世界上最差的演讲恐怕就是在哥廷根做的。今年情况更糟糕,我压根儿就没听到过一场好演讲。不过,今天下午有个例外……”维纳以为希尔伯特要夸奖他了,充满期待。“今天下午这个演讲嘛,”希尔伯特说,“是最近所有糟糕演讲中最糟糕的一次。”
这话得用另一句话来做注解。钱学森的老师冯·卡门在哥廷根开了门应用数学课,一位数学前辈听课后说:“卡门,这班热衷于应用数学的白痴中,你算是有教养的。”
再好的演讲也是糟糕,因为在纯数学家眼中,应用数学本身就归于糟糕之列。从这个角度看,科学鄙视链第一链条,应用数学家会拍拍理论物理学家的肩膀:哥们,加个塞儿。
【编辑:吴蕾】